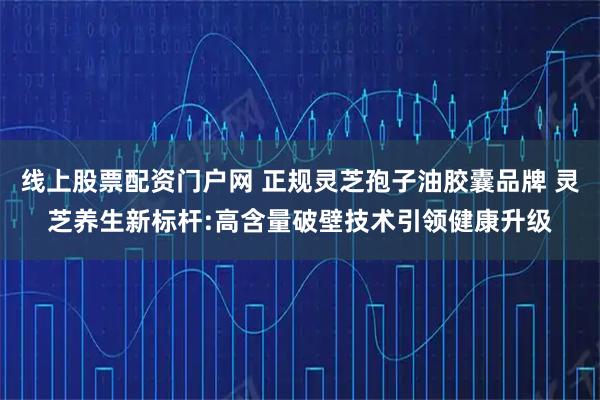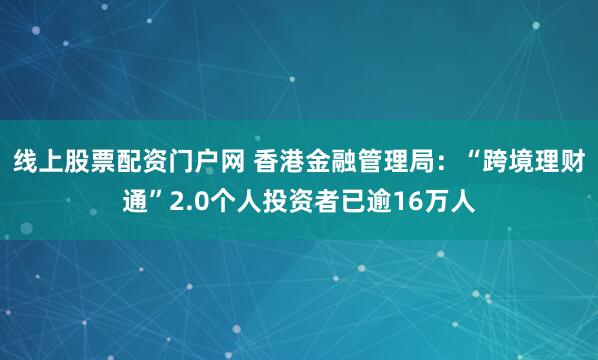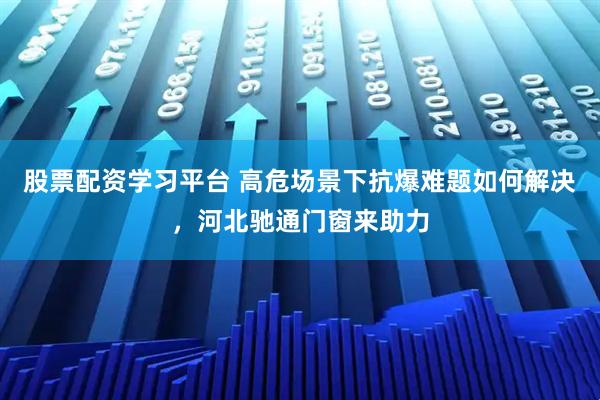功过是非,究竟由谁评说?是青史竹简上冰冷的墨迹正规在线炒股配资知识门户,还是万家灯火里温暖的口碑?
道德经有云:“大方无隅,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”真正的丰功伟绩,有时并不显露于外,真正的英雄,或许根本无名无姓。
历史的长河正规在线炒股配资知识门户,泥沙俱下。我们看到的,往往是帝王将相的光辉,是载入正史的赫赫战功。然而,在那光辉的背后,是否总有那么一些身影,被刻意地隐去,被无情地遗忘?
他们或许背负了世人无法理解的骂名,或许承受了不能言说的委屈,只为换取一个时代的安稳,一方水土的太平。他们的名字,未曾镌刻于碑石,却早已融入了山川河流,融入了百姓的寻常岁月里。
在五代十国那段纷乱的岁月里,吴越国偏安一隅,国泰民安,俨然一方乐土。其开国之君钱镠,以“保境安民”为国策,兴修水利,发展农桑,被后世誉为“海龙王”。然而,在他辉煌一生的尽头,在那间只剩下最后烛火摇曳的寝宫里,却藏着一个让英雄扼腕,让君王垂泪的秘密。这个秘密,关乎一个人的名节,更关乎吴越国数十年的国运根基。

01
后唐长兴三年,吴越国都城钱塘。
王宫之内,一片死寂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和一种名为“等待”的沉重。
吴越王钱镠,这位从盐贩一路走到裂土封王的传奇君主,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御榻之上。他那曾经能拉开强弓、挥动铁鞭的魁梧身躯,如今已如风中残烛,只剩下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。
他的儿子们,那些未来将要继承这片土地的王孙贵胄,一个个身着朝服,跪在榻前,脸上写满了程式化的悲戚。朝中的重臣,文官武将,则分列两侧,垂首肃立,偌大的寝宫,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跳声。
所有人都知道,这位庇护了吴越百姓数十年的“海龙王”,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。
太医颤巍巍地收回了诊脉的手,对着诸位王子,绝望地摇了摇头。
压抑的啜泣声,终于忍不住从人群中传来。
“父王”太子钱元瓘膝行向前,声音哽咽。
然而,病榻上的钱镠,双眼依旧紧闭,干裂的嘴唇却在微微翕动。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,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在呼唤着什么。
“水水”
钱元瓘心中一痛,连忙端过一旁的温水,用汤匙小心翼翼地送到父亲嘴边:“父王,儿臣在这里,您要喝水吗?”
几滴水润湿了钱镠的嘴唇,他却猛地偏过头,枯瘦的手在锦被上摸索着,似乎想要推开什么。他的眼睛,豁然睁开了一道缝隙。
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!浑浊,却又带着一丝焦灼的清明,仿佛穿透了眼前的所有人,望向了一个遥远的地方。
“水丘昭券”
这一次,三个字,虽然微弱,却异常清晰。
寝宫之内,瞬间陷入了更深的寂静。
所有人都面面相觑,脸上写满了茫然和困惑。
水丘昭券?
这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。在场的王公大臣,饱读诗书的文臣,久经沙场的老将,没有一个人听说过。
是某位被遗忘的故人?还是一个杜撰的名字?
太子钱元瓘也愣住了,他俯下身,轻声问道:“父王,您说的是谁?是宫里的旧人吗?儿臣马上派人去找!”
钱镠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他费力地摇着头,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竟然涌上了一层水光。他环视着跪在眼前的儿子和臣子,眼神里流露出的,不是欣慰,不是不舍,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烦躁和疏离。
“都都出去”
他的声音嘶哑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“父王!”
“滚!”
一声低吼,耗尽了钱镠最后的力气。他剧烈地咳嗽起来,脸色涨得紫红,仿佛随时都会断气。
众人大惊失色,不敢再违逆。太子钱元瓘只得含泪叩首,带着一众兄弟和大臣,一步三回头地退出了寝宫。
厚重的宫门缓缓关上,将内外隔绝成了两个世界。
门外,是即将迎来新主的吴越国。
门内,只剩下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,和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。
钱镠的亲信大太监福安,是唯一被允许留下的人。他从钱镠少年时便跟随左右,主仆二人,情同手足。
“王上”福安跪在榻边,老泪纵横。
钱镠的呼吸稍稍平复了一些,他用尽力气,抓住福安的手,那力道,竟让福安感到一阵生疼。
“福安快去西溪找他”
“找水丘昭券”
“告诉他,我我不行了临走前只想再见他一面”
“快去!用我的王令金牌,不管他愿不愿意见我,把他绑也要绑来!”
福安浑身一震。
西溪?那个地方,在钱塘城西,是一片芦苇丛生、人烟稀少的湿地。早年间,那里是流放犯官和安置麻风病人的地方,素来被城中百姓视为不祥之地。
而水丘昭券这个名字,福安的记忆深处,似乎有过一丝模糊的印象。那似乎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。一件被王上亲自下令,从所有文书档案中抹去,永远不准再被提起的旧事。
与那件事一起被抹去的,似乎就有这个名字。
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王上心心念念的,不是自己的江山社稷,不是子孙后代,而是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名字?
福安不敢多问,他看到钱镠眼中那恳求与命令交织的目光,心如刀绞。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,从钱镠的枕下,摸出那面代表着吴越国最高权力的金牌,揣入怀中。
“王上,您撑住!老奴就是拼了这条命,也一定把人给您带回来!”
福安连滚带爬地冲出寝宫,不顾门外太子和大臣们惊疑的目光,嘶声喊道:“备马!快备最好的马!”
夕阳的余晖,将钱塘城的轮廓染成一片悲壮的金色。福安的身影,消失在宫城的尽头。
寝宫之内,钱镠的目光,始终望着窗外西边的方向。他的嘴唇,还在无声地念着那个名字。
水丘昭券。
昭券
仿佛念着这个名字,就能减轻他心中那份压抑了几十年的沉重与愧疚。

02
时光倒流回三十多年前。
那时的钱镠,还未称王,只是被唐廷册封的镇海、镇东两军节度使,是这片土地的实际主宰。
彼时的钱塘,远不如后世繁华。它虽为吴越首府,却常年笼罩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下钱塘江大潮。
每年八月,大潮奔涌而至,摧枯拉朽,吞噬良田,卷走房屋,无数百姓流离失所,甚至葬身鱼腹。江海之患,是悬在所有钱塘百姓头上的一把利剑,也是钱镠心头最大的一块病。
他曾多次征集民夫,效仿前人,修筑捍海石塘。然而,钱塘江水势之凶猛,远超想象。土石筑成的堤坝,在大潮面前,脆弱得如同沙堡,一次次被冲垮,耗费了无数钱粮人力,却收效甚微。
那一年的大潮,来得尤其凶猛。
城西的堤坝再次决口,浊浪滔天,半个钱塘城都泡在了水里。钱镠站在城楼上,看着城外一片汪洋,听着百姓凄厉的哭喊,心如刀割。
他当众立誓,若不能根治潮患,他钱镠有何面目,做这吴越之主!
为此,他广发榜文,遍寻天下能人异士,凡能献策治水者,无论出身,不问过往,一律重赏。
一时间,应募者云集。有自诩通晓阴阳五行的方士,有经验丰富的老工匠,也有满腹经纶的读书人。钱镠一一接见,得到的方案却大同小异,无非是加固堤坝,深挖河道,这些,他早就试过了。
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,一个年轻人,拿着一份图纸,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这个人,就是水丘昭券。
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,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,身形清瘦,面容俊秀,但眉宇间却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执拗。
他不是方士,不是工匠,也不是读书人。他说,他只是一个山野村夫,常年在江边观察水文,对潮汐的规律,略知一二。
他一开口,就否定了之前所有人的方案。
“节帅,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异常坚定,“钱塘潮患,病根不在堤,而在江心。江道淤塞,水流不畅,潮水至此,受阻而壅高,故而势大。单纯加固堤坝,乃是扬汤止沸,非釜底抽薪之策。”
钱镠精神一振。这个说法,倒是新颖。
“那依你之见,该当如何?”
水丘昭券缓缓展开手中的图纸。那上面,没有复杂的堪舆阵法,也没有精密的工程构造,只有一道道看似随意的曲线。
“欲治其水,先顺其势。我们需要的,不是去堵,而是去疏。”
他指着图纸说道:“可在江心,顺着水流的走向,用巨石和铁水浇筑,筑起一道鱼脊。这道鱼脊,看似阻碍,实则能将奔涌的潮水分成两股,削弱其正面冲击之力。同时,再于堤坝之外,开凿数条引水支流,将潮水引入内陆湖泊。如此,一分二,二分四,层层削弱,则潮势自减。”
这个想法,大胆,甚至有些疯狂。
在汹涌的江心筑堤?这简直是天方夜谭!
在场的一位老工匠当即反驳:“年轻人,你可知在江心施工,有多艰难?莫说筑堤,便是打下一根木桩,也会被瞬间冲走!你这是纸上谈兵!”
水丘昭券却不慌不忙,淡淡地说道:“寻常木石,自然不行。但若用石笼之法,或可一试。”
“石笼?”众人又是一阵茫然。
“以巨竹编成笼,内填满山石,再以数艘大船拖拽,沉于江心预定之处。石笼沉底,层层叠加,自成一体。待石笼稳固,再以铁水浇灌其缝隙,使其凝为一体,则坚不可摧。”
这个“石笼沉江”的法子,闻所未闻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在痴人说梦。
钱镠却陷入了沉思。
他从水丘昭券的眼中,看到了一种无比的自信。那不是狂妄,而是一种基于精密计算和无数次观察后得出的笃定。
他详细询问了石笼的编法、尺寸,沉江的时机,以及如何保证位置精准。水丘昭券对答如流,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清清楚楚,仿佛他已经在脑海里,将这道捍海长堤,修筑了千百遍。
钱镠的心,动了。
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放手一搏!
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,力排众议,当场拍板,将治理潮患的全权,交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。
他封水丘昭券为“都水使”,拨给他三千精兵,无数钱粮,让他全权负责此事。
这个决定,在当时的钱塘,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一个来历不明的毛头小子,一无功名,二无资历,仅凭几张图纸,一番大话,就得到了节度使如此的信任?
一时间,流言四起。有人说,这水丘昭券,怕不是什么会蛊惑人心的妖人。也有人说,节帅是被潮患冲昏了头,病急乱投医。
朝中反对的声浪,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几位元老重臣,甚至以辞官相逼。
钱镠顶住了所有的压力。
他只对众人说了一句话: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我信他,也请诸位,信我一次。”
于是,在钱塘江畔,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,在无数质疑的目光中,轰轰烈烈地开始了。
水丘昭券没有辜负钱镠的信任。
他吃住都在江边的工地上,亲自带着工匠测量水文,设计竹笼,指挥民夫开山采石。他仿佛不知疲倦,整个人都投入到了这项疯狂的计划之中。
他瘦削的身影,日夜穿梭在泥泞的工地上,很快,就和那些普通的民夫,再无两样。
钱镠时常会微服私访,站在远处,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看到水丘昭券为了一个数据的精准,顶着寒风在江边站立一天一夜;看到他为了鼓舞士气,亲自跳进冰冷的江水中,与民夫一起打下木桩。
钱镠的心中,愈发肯定,自己没有看错人。
然而,工程的难度,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江心水流湍急,漩涡密布。第一批沉下的石笼,很快就被暗流冲得无影无踪。数万斤的巨石,投入江中,连个水花都见不到。
几次失败下来,军心、民心,都开始动摇。
那些原本就反对的官员,更是找到了由头,纷纷上书,请求钱镠立刻停止这项“劳民伤财”的荒唐之举,并严惩“妖言惑众”的水丘昭券。
就连钱镠自己,也开始怀疑,这个决定,是否真的太过草率。
那天深夜,他独自一人,来到了水丘昭券的营帐。
营帐里,灯火通明。水丘昭券正趴在一张巨大的图纸上,用朱笔飞快地计算着什么。他的头发凌乱,眼窝深陷,布满了血丝,整个人都像是被抽干了精气。
看到钱镠进来,他只是微微抬了下头,沙哑地说了句:“节帅来了。”便又埋头于图纸之中。
钱镠坐在一旁,沉默了许久,终于开口道:“昭券,若是事不可为,也不必强求。钱塘的百姓,会记着你的这份心。”
他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。
水丘昭券的笔,停住了。
他抬起头,通红的眼睛,直直地看着钱镠,一字一句地说道:“节帅,还记得我第一次见您时说的话吗?”
钱镠一怔。
“我说,病根不在堤,而在江心。如今看来,是我错了。”
水丘昭券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奇异的颤抖。
“病根,既不在堤,也不在江心。”
“那在哪里?”钱镠下意识地问道。
水丘昭券缓缓站起身,走到营帐门口,掀开帘子,望向那片在月光下奔腾不息的黑色江面。
他沉默了许久,才用一种近乎梦呓般的声音,说出了一句让钱镠毛骨悚然的话。
“病根在龙王爷的心里。”

03
“病根在龙王爷的心里。”
这句话,如同一道惊雷,在钱镠的脑海中炸响。
他霍然起身,厉声喝道:“水丘昭券!你胡说什么!子不语怪力乱神,你是要本帅去求神拜佛吗?”
作为一方主宰,钱镠虽敬畏天地,却从不信鬼神之说。他信奉的,是人定胜天。
水丘昭券缓缓转过身,脸上没有丝毫惧色,反而带着一种悲悯的神情。
“节帅,我并非让您去求神拜佛。”
“钱塘江潮,千年如此,其势之凶,早已超出了人力所能抗衡的范畴。我们筑堤,它便冲垮;我们疏浚,它便改道。这江水,仿佛有自己的意志,有自己的怨气。”
“怨气?”钱镠皱起了眉头,他觉得水丘昭券今晚的话,越来越离谱。
“对,怨气。”水丘昭券的声音压得极低,“这些天,我查阅了所有关于钱塘江的古籍。发现一个规律,每隔六十年,便会有一次前所未有的惊天大潮,足以将整个钱塘夷为平地。而每一次大潮之后,江海便会平息一个甲子。算算时间,下一次惊天大潮,就在明年。”
“而要平息这怨气,安抚这江海,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水丘昭券的目光,变得无比深邃,仿佛两口不见底的古井。
“那便是献祭。”
钱镠的心,猛地一沉。
“献祭?”他想到了那些民间愚昧的传说,用活人祭祀河神,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,“荒唐!我钱镠治下,绝不容许此等伤天害理之事!”
“不,节帅,您误会了。”水丘昭券摇了摇头,“我说的献祭,不是用无辜百姓的性命。”
他顿了顿,似乎在斟酌着词句,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。
“而是用一道罪,去献祭。”
“用罪献祭?”钱镠彻底糊涂了。
“节帅,您想成就一番霸业,庇护这吴越百姓,就必须要有雷霆手段。有些事,史书上看起来光鲜亮丽,但其背后,必然有见不得光的阴暗。这,就是成大事者必须背负的原罪。”
“欲平江海,先要让江海看到我们的诚意。这诚意,不是金银,不是牛羊,而是一桩足以震动天下,足以让鬼神为之侧目的大恶行。我们要犯下一桩罪,一桩能让钱塘江的怨气相形见绌的罪!”
水丘昭券的话,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,狠狠地插进了钱镠的心脏。
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清瘦的年轻人,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他一直以为水丘昭券是个治水的奇才,却没想到,他的心里,竟然藏着如此惊世骇俗的魔鬼念头。
“你的意思是”钱镠的声音在发抖,“要我去制造一桩冤案?去杀一个不该杀的人?以此来献祭?”
水丘昭券没有直接回答,他从怀中,取出了一卷发黄的羊皮纸,递到钱镠面前。
“节帅,这是我这些天重新制定的方案。石笼之法,依然可用。但沉江的时机,用的材料,以及奠基的方式,需要改一改。”
钱镠颤抖着手,接过那卷羊皮纸。
他缓缓展开,只看了一眼,便如遭雷击,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
那上面,除了更加精密复杂的工程图纸外,还有一行用朱砂写就的小字。
字迹不大,却触目惊心。
那是一份名单,一份死亡的名单。
名单上的人,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囚犯,也不是什么敌国的奸细。他们是之前几次筑堤失败的工匠头领,是负责调度钱粮的官员,甚至还有几个曾经上书弹劾过水丘昭券的朝中老臣。
在名单的最后,水丘昭券用一种近乎疯狂的笔触,写下了他的计划。
他要钱镠以“贪墨钱粮,贻误工期,致使万民遭灾”的罪名,将名单上的所有人,公开处斩。
并且,要在行刑的那一天,取他们的鲜血,混入铁水之中,用以浇灌石笼。
他将此法,称之为“血祭龙王”。
“疯子你真是个疯子!”钱镠一把将羊皮纸狠狠地摔在地上,指着水丘昭券,气得浑身发抖,“他们他们都是为我吴越出过力的人!有几位还是跟我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!我怎么能我怎么能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献祭,就杀了他们!”
“节帅!”水丘昭券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重重地磕了一个头,“妇人之仁,难成霸业!这些人,不死于您的王法,也终将死于明年的大潮!与其让他们和满城百姓一起葬身鱼腹,不如用他们的罪,换取吴越国百年的安宁!”
“这不是罪!这是构陷!是屠戮功臣!”
“在百姓眼里,他们就是罪人!筑堤失败,他们难辞其咎!只要您一道王令,他们就是贪官污吏,就是千古罪人!百姓不会同情他们,只会拍手称快!他们会认为,是您为民除害,才感动了上苍,平息了潮患!”
“至于历史”水丘昭券抬起头,眼中闪烁着一种狂热的光芒,“历史,是由胜利者书写的!只要捍海石塘能建成,只要吴越国能长存,您就是万民称颂的圣君!谁又会去在意,这堤坝之下,埋着几具无辜的白骨?”
钱镠呆住了。
他看着跪在地上,神情狂热的水丘昭券,感觉自己仿佛在凝视一个深不见底的魔鬼。
这个计划,太恶毒,太阴狠,却又该死的有效。
他知道,只要他点头,钱塘江的潮患,或许真的能被根治。他将成为吴越百姓心中真正的“海龙王”,他的功绩,将千古流传。
但代价,是他的良心。
是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的性命,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,是他的双手,将永远沾满洗不净的鲜血。
他该怎么选?
是守住自己为人的底线,眼睁睁地看着子民涂炭,基业被毁?
还是饮下这杯魔鬼递来的毒酒,用他人的鲜血和冤屈,去铸就自己不朽的功业?
营帐之内,油灯的火苗,在夜风中疯狂地跳动,将两人的影子,拉得忽长忽短,如同鬼魅。
钱镠的内心,在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。
他闭上眼睛,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决堤之时,百姓那凄厉的哭喊。他又想起了水丘昭券那句话:“欲平江海,先要让江海看到我们的诚意。”
许久之后,他缓缓睁开双眼,眼中所有的挣扎和犹豫,都已褪去,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冰冷。
他弯下腰,捡起了地上的那卷羊皮纸,用指尖,轻轻抚过上面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。
他的声音,沙哑得仿佛不是自己的。
“昭券,这个计划,若要施行必须有一个人,来背负这所有的罪孽。”
水丘昭券抬起头,眼中没有丝毫意外,只有一片决然。
“臣,愿为节帅,为吴越百姓,背负这万古骂名。”
“不。”钱镠摇了摇头,他的目光,落在了羊皮纸的末端,那个落款的名字上。
“这个计划,是你制定的。但这个罪,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背。”
他拿起朱笔,在那份名单的最后,缓缓写下了两个字。
那两个字,不是别人的名字。
而是钱镠。

寝宫之内,死一般的寂静。
福安已经走了很久,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也已消失,唯有几盏昏黄的宫灯,映照着钱镠那张苍老而布满沟壑的脸。
他的思绪,从三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抉择中,缓缓抽离出来。
那份“血祭龙王”的计划,最终还是被执行了。只是,执行的方式,比水丘昭券最初的设想,更加隐秘,也更加残酷。
那一天,钱塘城愁云惨淡。几十名官员和工匠头领,以“贪腐渎职”的罪名被推上了刑场。百姓们义愤填膺,高呼着“节帅英明”。
没有人知道,那所谓的“罪证”,不过是几本伪造的账册。更没有人知道,在这场“为民除害”的盛大表演背后,真正肮脏的交易和牺牲,才刚刚开始。
钱镠得到了他想要的捍海石塘。那道用无数金钱、血汗,以及不能言说的“罪孽”浇筑而成的长堤,如同一条巨龙,牢牢地锁住了钱塘江的怒涛,换来了吴越国此后数十年的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他也如愿成为了百姓口中万世传颂的“海龙王”。
可是,水丘昭券呢?
当钱镠的功绩被载入史册,被万民敬仰之时,那个真正奠定了吴越国百年基业的年轻人,却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,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的名字。
他去了哪里?他又背负了什么?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打断了钱镠的回忆。
宫门被缓缓推开,一股夹杂着水汽和草木气息的微风,吹了进来。
福安的身后,跟着一个佝偻的身影。
那人穿着一身粗布麻衣,头发花白,脸上布满了风霜的刻痕,一双脚赤着,沾满了泥土。他看起来,就像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乡野老农。
然而,当他抬起头,与钱镠四目相对的那一刻,整个寝宫的空气,仿佛都凝固了。
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!平静,淡漠,古井无波,仿佛这世间的一切繁华、荣耀、生死、荣辱,都与他再无干系。
钱镠那双枯瘦的手,猛地抓紧了锦被,他的身体,开始剧烈地颤抖。
他挥了挥手,示意福安退下。
厚重的宫门再次关上。
偌大的寝宫,只剩下他和这个从西溪泥沼里走出来的老人。
钱镠挣扎着,想要坐起身来,却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浑浊的泪水,终于抑制不住地从他的眼角滚落,浸湿了身下的龙枕。
他张了张嘴,喉咙里发出的,却是如同野兽哀鸣般的呜咽。
他握住了水丘昭券那只粗糙、冰冷,满是老茧的手。那只手,曾经画出过奠定吴越国百年基业的图纸,也曾经,为他签下过一份魔鬼的契约。
数十年的君臣之义,兄弟之情,所有的秘密,所有的愧疚,所有的感恩,在这一刻,尽数化作了决堤的洪流。
这位一生要强的君王,在这位被历史彻底遗忘的老人面前,终于像个孩子一样,痛哭失声。
04
老人缓缓抬起手,用那满是泥垢和裂纹的指腹,轻轻拭去钱镠眼角的泪水。他的动作很慢,很轻,仿佛在触摸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“王上,”他的声音沙哑,像是两块粗糙的石头在摩擦,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,“江潮有起落,人生有生死。您守着这片土地,守了几十年,也该歇歇了。”
钱镠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,他死死抓着老人的手,仿佛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“昭券我对不住你我我让你背负了不该背负的骂名,却抹去了你本该不朽的功绩”
“是我是我窃取了你的荣耀,让你让你像个孤魂野鬼一样,在这世上活了三十年!”
这位戎马一生、从未在敌人面前低过头的君王,此刻泣不成声。
水丘昭券闻言,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里,终于泛起了一丝涟漪。他摇了摇头,脸上没有怨恨,没有委屈,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。
“王上,您说错了。”
“您没有窃取任何东西。那份荣耀,从一开始,就不是我的。”
钱镠猛地一怔,泪眼婆娑地看着他,不解其意。
水丘昭券扶着床沿,缓缓坐下,目光仿佛穿透了华丽的宫墙,望向了三十多年前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。
“您还记得那份血祭龙王的名单吗?”他轻声问道。
钱镠的身子剧烈一颤,那份用朱砂写就的名单,是他一生的梦魇。
“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”
“那些人,都死了吗?”水丘昭券又问。
钱镠闭上了眼睛,痛苦地摇着头:“没有一个都没有死”
这是他和水丘昭券之间,埋藏得最深的秘密。
当年,钱镠在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,他告诉水丘昭券,他可以为了吴越的百姓,背负千古骂名,却不能用无辜者的鲜血,来玷污自己的双手。
于是,他们制定了一个更加疯狂,也更加仁慈的计划。
那场轰动钱塘的公开处斩,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
刑场上被斩首的,是早已被判了死刑的江洋大盗,他们被换上了官员的服饰,在百姓的怒吼声中,成了替罪的羔羊。
而那份名单上的几十名官员和工匠,则在前一夜,被秘密“赐死”。他们喝下的,不是毒酒,而是一碗能让人陷入假死的汤药。
当他们的“尸体”被运出城外,他们的家人接到的是他们“畏罪自杀”或“暴病而亡”的死讯。
而后,这些人被悄悄送往吴越国最偏远的山村,被赐予新的身份,发给足够安度余生的田产和金钱,但被勒令,此生此世,永不得再踏入钱塘半步,永不得再提及自己的过往。
他们牺牲的,不是性命,而是他们的名字、他们的官职、他们前半生的所有荣光。
他们从青史留名的功臣,变成了在乡野间默默无闻的富家翁。
而那所谓的“血祭”,用来浇灌铁水的,也并非人血,而是钱镠命人从屠宰场收集来的牛羊之血。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上,由道士作法,洒入熔炉,以慰“龙王”。
一场弥天大谎,骗过了所有人。
它既用一场盛大的“罪恶”表演,凝聚了民心,震慑了宵小,又用一种残酷的仁慈,保全了那些人的性命。
“王上,您没有杀他们。”水丘昭券的声音将钱镠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
“您用自己的王位和声誉做赌注,保全了他们的性命。这份仁心,天下君王,几人能有?”
“可是”钱镠的声音依旧颤抖,“他们的名节毁了!后世史书,只会记载他们是贪官污吏!”
水丘昭券笑了,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,露出了一丝极淡的,却无比温暖的笑意。
“史书?史书算什么?”
“我后来偷偷去看过他们中的几位。那个当初负责调度钱粮的张大人,成了远近闻名的善人,他用您赐予的金钱,在家乡修桥铺路,救济孤寡。乡亲们都叫他张大善人,没人知道他曾经是什么贪官。”
“还有那个王工头,他带着一身的本事,在山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,还改进了农具,让一整个村子都富裕了起来。他的牌位,至今还供在村里的祠堂里,受着百家香火。”
“王上,”水丘昭券的目光,重新落在钱镠的脸上,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您给他们的,不是毁掉的名节,而是一段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。青史竹简上的几个字,哪里比得过万家灯火里的口碑?”
钱镠呆住了。
他从未想过这些。三十年来,他一直活在“屠戮功臣”的愧疚之中,却不知道,那些被他“牺牲”掉的人,在另一个地方,以另一种方式,活出了真正的价值。
他心中的一块巨石,仿佛被挪开了一角,透进了一丝光亮。
但他看着眼前衣衫褴褛,形容枯槁的水丘昭券,那丝光亮,又被更深的愧疚所淹没。
“可是你昭券,他们都活出了自己,那你呢?”
“你为吴越立下了不世之功,却要背负妖言惑众的恶名,隐姓埋名,藏身于泥沼之中这不公!这不公啊!”
水丘昭券脸上的笑容,慢慢敛去。
他沉默了片刻,才缓缓开口。
“王上,这便是我们当年,共同的选择。也是我的名字,永远不能出现在史书上的,真正原因。”

05
“我的名字,不能出现在史书上”水丘昭券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悠远,“因为在您为那几十位功臣平反昭雪的那一刻,水丘昭券这个名字,就必须成为吴越国最大的罪人。”
钱镠的呼吸,猛地一滞。
他想起来了。
捍海石塘建成之后,潮患被彻底根治,钱塘一片欢腾。
然而,那些被“牺牲”的官员家属,却依旧背负着“罪臣之后”的污名,在钱塘城中抬不起头。
钱镠于心不忍。
同时,朝中也有一些明眼人,对那场仓促的“定罪”和“行刑”心存疑虑。水丘昭券这个凭空出现,又凭空得到重用的人,更是成了众矢之的。
为了彻底了结此事,也为了给那些“牺牲者”一个交代,钱镠和水丘昭券,演了这出戏的最后一幕,也是最关键的一幕。
钱镠下令,重审“贪腐大案”。
很快,调查结果便“水落石出”:所谓的贪腐,纯属子虚乌有。一切,都是那个“都水使”水丘昭券的阴谋!
是他,妖言惑众,蛊惑君王,以“血祭”之邪说,构陷忠良,意图动摇国本!
一时间,舆论哗然。
百姓们恍然大悟,原来那些被杀的官员是无辜的!原来真正的恶人,是那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!
而吴越王钱镠,则是一位被蒙蔽的圣君。他虽然一度被奸人迷惑,但最终幡然醒悟,拨乱反正,为忠臣洗刷了冤屈,更显其英明神武。
于是,在一场更加盛大的审判之后,水丘昭券被定为“国之妖孽”,判处流放,其名被从所有官方文书、档案、功劳簿中彻底抹去,并下令,吴越国境之内,任何人不得再提起“水丘昭券”四字,违者,以同罪论处。
捍海石塘的盖世奇功,自然而然地,全部归于了英明神武的吴越王钱镠一人。
自此,钱镠的声望,达到了顶峰。他不仅是治水英雄,更是一位知错能改,不护短,不讳过的圣君。
而水丘昭券,则成了那个必须被遗忘的,肮脏的注脚。
“您需要一个完美的功绩,吴越国需要一个完美的君主。”水丘昭券平静地叙述着,“而一个完美的英雄故事里,必须有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。我,就是那个魔鬼。”
“这个角色,只有我能演,也必须由我来演。”
“因为,血祭龙王这个疯狂的念头,确确实实,是从我的脑子里想出来的。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去做,但那个因,是我种下的。所以,这个果,理应由我来承担。”
“王上,您背负的是欺骗天下的愧疚,而我背负的,是构陷忠良的骂名。我们一个在明,一个在暗,共同扛起了这片江山。这很公平。”
公平?
钱镠的心,像被无数根钢针狠狠扎刺。
这哪里是公平!
他钱镠,享尽了人间的尊荣与赞美,夜里做的,却是不见天日的噩梦。
而水丘昭券,一个本该名垂青史的天才,却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,躲在无人问津的角落,听着世人对自己的唾骂,看着别人享受着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。
他失去的,不仅仅是名声,是功绩,是他的一切!
“昭券”钱镠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“我我可以为你正名!我现在就下旨,告诉天下人,你才是真正的英雄!是我,是我钱镠,窃取了你的功劳!”
他挣扎着,似乎想要呼唤门外的福安。
“不可!”
水丘昭券猛地按住了他的手,那双平静的眼睛里,第一次露出了急切而严厉的神色。
“王上!万万不可!”
“历史,一旦写定,就不能再改了!您是吴越国的定海神针,您的声誉,就是吴越国的国运!若是让天下人知道,您为了功绩,曾与人合谋,上演了这么一出欺君罔世的大戏,那民心何在?国法何存?”
“您的一世英名,会毁于一旦!吴越国的根基,会因此动摇!我们三十多年前做出的所有牺牲,都将变得毫无意义!”
水丘昭券的每一句话,都像一记重锤,狠狠地敲在钱镠的心上。
是啊,他怎么忘了。
这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,这关系到整个吴越国的安危。
一个谎言,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。他们当初选择走上这条路,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
钱镠瘫软在御榻上,浑浊的眼中,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和悲凉。
他赢得了天下,却输给了自己的良心。他成了百姓的“海龙王”,却成了一个连自己兄弟的名分都无法给予的懦夫。
“我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?”他喃喃地问道,声音里充满了乞求,“金钱?土地?还是别的什么?”
他只想,在临死之前,为这个被自己亏欠了一生的人,做一点点补偿。
水丘昭券看着他,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他站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了那扇紧闭的窗户。
一股带着湿润泥土芬芳的晚风,吹了进来,卷起了他花白的鬓角。
“王上,您看。”
他指着窗外。
远处,钱塘城的万家灯火,已经次第亮起,如同一片璀璨的星海,在夜幕下静静地流淌。
隐约间,还能听到街市上传来的喧闹声,孩童的嬉笑声,夫妻间的呢喃声。
那声音,充满了世俗的,温暖的,鲜活的生命力。
“您看这满城的灯火,您听这人间的声响。”
水丘昭券转过头,脸上再次露出了那种淡然而满足的微笑。
“这,就是您给我的,最好的补偿。”

06
“这满城灯火,便是最好的补偿。”
这句话,如同一道温暖的溪流,缓缓淌过钱镠几近干涸的心田。
他怔怔地看着窗外那片璀璨的星海,看着那一片由他亲手守护下来的安宁与繁华,浑浊的眼睛里,渐渐有了一种名为“释然”的光。
是啊。
他还在纠结什么呢?
功过是非,究竟由谁评说?
不是青史竹简,不是王侯将相,而是这万家灯火,是这人间寻常。
他和水丘昭券,一个在庙堂之上,一个在江湖之远;一个顶着圣君的光环,一个背着妖人的骂名。
他们就像一个人的两面,一面是光,一面是影。
光鲜为世人所见,荣耀加身;影子则被踩在脚下,默默无闻。
但光和影,本就是一体,缺一不可。没有影子的衬托,光便失去了形状;没有光的照耀,影子也无从谈起。
他们共同的目标,从始至终,都只有一个便是守护这片土地,守护这满城的灯火。
如今,他们做到了。
这就够了。
“昭券”钱镠的呼吸,变得平缓起来,他眼中的焦灼与愧疚,正在一点点褪去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
他吃力地从自己的腰间,解下了一块温润的古玉。那块玉,通体洁白,上面只刻着两个古朴的篆字:钱镠。
这是他少年时,母亲留给他唯一的遗物,伴随他从一个盐贩子,一路走到裂土封王,从未离身。
“这个,你拿着。”他将玉佩,塞进水丘昭券的手中,“它不是王令,不是封赏。它只是钱镠给兄弟的一点念想。”
水丘昭券低头看着掌心那块带着君王体温的玉佩,沉默了许久。
他没有拒绝。
他知道,这是钱镠在偿还他心中最后一笔债。他若不收,钱镠死不瞑目。
他将玉佩紧紧攥在手心,然后,对着病榻上的钱镠,缓缓地,深深地,弯下了腰。
这一拜,没有君臣之礼,没有尊卑之别。
只是一个朋友,对另一个即将远行的朋友,最郑重的告别。
“王上,保重。”
水丘昭券直起身,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
他转过身,佝偻着背,一步一步,向着宫门外走去。
他的身影,就如他来时一样,悄无声息,平凡得像一滴水,融入了深沉的夜色之中。
钱镠的目光,一直追随着他,直到那扇厚重的宫门,缓缓关上,将内外,再次隔绝成两个世界。
门外,是水丘昭券选择的江湖。
门内,是钱镠即将放下的庙堂。
钱镠缓缓闭上了眼睛,脸上,带着一丝满足的,淡淡的微笑。
压在他心头三十多年的巨石,终于被彻底搬开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宁静。
他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,那个站在江边,意气风发的年轻人。
他又仿佛看到了那道坚不可摧的捍海长堤,和那片长堤之后,一望无际的丰饶田野。
他的耳边,仿佛又响起了水丘昭券最后的那句话。
“我的碑,是那道长堤。我的名,是这万家灯火。”
真好。
真好啊

后唐长兴三年冬,吴越王钱镠,薨。
据史书记载,王上临终前,神态安详,面带微笑,仿佛只是沉沉睡去。太子钱元瓘率百官入内,只见先王手中,空无一物,唯有目光,始终朝向西方。
钱镠的传奇一生,被载入史册。他保境安民,兴修水利,被后世誉为“海龙王”,其修建的钱塘石塘,更是被视为千古奇功,福泽后世近千年。
在他的官方传记里,没有任何关于“水丘昭券”的记载。只有一个语焉不详的注脚,提到早年曾有“妖人”作祟,幸得王上明察秋毫,才未酿成大祸。
许多年后,西溪的芦苇荡里,人们发现了一座无名孤坟。坟前没有墓碑,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包。据说,曾有人在很多年前,见过一个孤僻的老人住在那儿,他时常一个人坐在水边,迎着朝阳,望着钱塘城的方向,一坐就是一天。
历史的长河,奔流不息。有些名字,被镌刻于碑石,供人瞻仰;有些名字,则被刻意遗忘,沉入泥沙。然而,真正的丰功伟绩,从不依靠冰冷的墨迹来证明。那矗立千年的长堤,那世代安居的百姓,那万家灯火的温暖,便是对那些无名英雄,最好,也最不朽的纪念。
极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